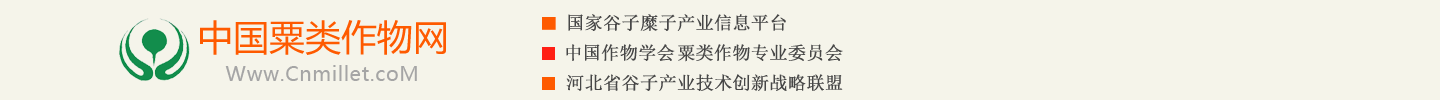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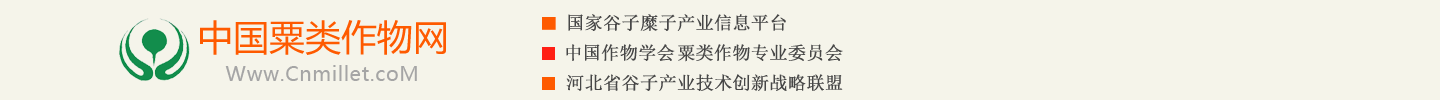


我祖籍武安城,我们这些小市民是靠买粮过日子的。曾记得小时候,粮店和市场上卖的几乎都是小米,其它豆类和小麦只不过是少量搭配。一般粮店是不售白面的,想吃白面需要到私人开设的小面房里买几斤,当时根本没有成袋面粉,像“富强粉”等袋面建国后武安才逐渐有了。当时只有南方才出产的大米,在武安稀如珍宝,价格昂贵,粮店里数量甚少,一般人平时都吃不起,逢年过节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得上。即使有钱人家也不大量买大米,成袋买的只有小米。武安常用的“量不上米不要丢了布袋”的俗语,无疑指的是小米。
小米不仅养育了世代武安人,武安人民还用小米支援了伟大的解放事业。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千万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人担驴驮小车推将大批小米送往前线。解放初期群众交公粮是小米,国家机关人员和教师挣的是小米,学生上学扛的是小米。当时我家里连一日三顿小米稀粥都保证不了,记得一次中午放学回家,火上熬着锅,父亲仍未买回小米,我看吃饭无望,便在炕上躺了一会儿悄悄上学走了。晚上回来,娘抱着我痛哭流涕,给父亲生了一场气。从此,我只好失学回家,扛起卖麻糖盘子继承了“父业”。不久,学校校长鲁彦、教导主任胡子兴亲自到我家,答应一天补助我一斤小米供我上学。也是,我便开始了早晨卖麻糖上午下午上学的“半工半读”生活。后来,学校干脆让我到学校吃饭,一日三餐小米饭,能顿顿填饱肚子,可算是“天堂”上的时光了(当时全校数百名学生,只有两名公费生)。相继上初师、后师、师专都是公费。我永世难忘,是党和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,培养了我。
武安人有个特点,久吃小米不腻,隔两天不吃就想得慌,所以自虐为“米虫”。
在全县无论城镇、农村,无处不吃小米,世世代代,古往今来,平常人家,一日早晚两顿小米稀粥,中午一顿小米干饭,几乎成为普遍模式。只是各家的稠稀和花样不同罢了。
对武安人来说,小米是没有“阶级性”的,穷家富户谁都喜欢。少数百万富翁,整日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,什么三鲜汤、莲子羹,也代替不了小米粥,只是比寻常人家吃的小米少一些。殷实人家,广有庄田,当年也是以小米为主粮。我农村有个解放后被划为“地主”成分的舅舅,家有一处亲砖瓦房,几十亩土地,惜财如命,只知攒钱买地,不肯花钱吃喝。我小时不断在那住几天,“享受”一下“地主生活”。他家每天早晚是小米稀粥和玉米面窝头,中午是小米干饭,四季吃的都是自家园中产的蔬菜,名曰“炒菜”,实则水煮。五六天中午才吃一顿“抿节”算是“改善”生活,还是离不开米面。只有初一、十五中午才吃一顿白面。有时候晚上做一点面片汤就是最高级的“夜宵”,只有舅舅有权享受,除了我这个年幼的小外甥沾光喝半碗外,其他人一概没份儿。像这样“米虫式”的“土地主”在武安农村最低的生活也比我家当年的‘地主生活’好得多!”过去不及我舅舅的穷人家当然是多数,一天能保持三顿小米饭就不错。锅开了没米下的人家也很多。我曾见过轧花工人和砖窑工人的生活,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干的是重体力活,身子的汗水用毛巾是无法擦的,都是用“汗刮子”(用绳拴在身上的小竹片或小木片)来刮。他们一日三餐都是小米夹生焖饭(米熟了不顶饿),几乎与蔬菜无缘,多数是饭里撒点盐面用来调味,以补充大量流失的汗水,偶尔来点盐拌葱花,那便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。一个个筋骨显露脂肪贫乏的汉子,端着大海碗狼吞虎咽,创造了小米饭最经济最豪放的吃法。
小米对武安人来说,不仅是人们的家常便饭,而且是“坐月子”的妇女、小孩和病人的“高级营养品”。产妇一个月的主食便是小米粥。断奶的孩子和病号,都要给他们灌点小米稀粥来补充营养,维持生命,在常人看来其作用不亚于输液输血。
长期远离家乡的武安人,最留恋家乡的饮食是小米饭。武安人去看望远离故土的亲戚朋友,带上点武安特产——“来武县谷”碾出的小米,那就是最珍贵最实惠的礼品了。前年我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医院,饭菜美味可口而富有营养,可是时间一长,高低调不起胃口,端起碗就想念家乡的小米粥。
在武安人的心目中,小米饭是就是饭的代名词。穷得无饭可吃就是“无米下锅”,生活富裕就是说“不愁锅里没米下”。如今要饭的只要钱不要吃的,过去要饭的手捧一个破瓷碗,“大爷大娘”叫半天,能要到半碗小米粥就谢天谢地了。武安有些地区有一种习俗,大年除夕吃好饺子以后,总还要熬点小米稀粥,喝点剩点,等大年初一再喝,名曰:“隔年饭”,象征来年五谷丰登,家有余粮,再好吃的饺子也代替不了小米饭的“职能”。“糠菜半年粮”的偏僻山区桃源沟,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桃源沟人坐天下,小米捞饭随便加。”像前苏联人把“土豆烧牛肉”当成理想的共产主义一样,他们把“小米捞饭随便加”幻想为最理想的生活了。现在武安的多数人家,当然是以大米白面为主粮了,被称为“米虫”的武安人永远不愿告别小米。